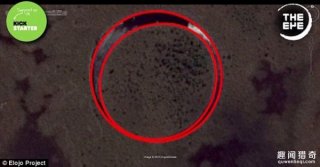难忘的遗憾
小时候,村里的碎娃们,还不会下象棋,也没有跳棋、军棋那类玩艺儿。我们常耍的,叫顶杠——是一种携带乡风村俗,饶有趣味儿的棋类游戏。就地取材,随处可玩。随便找个地儿,在地上横划几道印几,竖划几道印儿,成了方方正正的棋盘。棋子呢,石头子儿、杏胡儿、土疙瘩、柳条节、柴棒棒……只选两种不同的,就下起来了。

暑夏里一天,在我家院门楼里,遍被着凉爽的穿堂风,仲元捏指头大的石子,我折半寸长的柴棒棒,以石笔画棋盘,玩起了顶杠。正玩得入迷,我家的麻黄母鸡,咯咯蛋,咯咯蛋,叫开了。我妈在院里喊:
母鸡下蛋了,还不快捡回来!
那时候,家家院门外,都堆有粪堆。忽然兴起了全民写诗,村里家家户户和白灰在院墙外刷版面写,连庆家写的诗只两句:卫生工作大跃进,保证门上不堆粪。村人都养鸡,母鸡下了蛋,要喂一把精食,指望着多下蛋积攒了换油盐呢。我家的喂鸡的碎麦子,搁在院门里土墙上挂的担笼里,我却没去抓。只向粪堆那儿瞅了一眼,任母鸡叫死去,忙着顶杠。
见我蹲着不动,我妈又喊开了:
还不快去捡,天上老鹰在旋呢!
老鹰抓鸡蛋?笑话。我仍不管那,只埋头顶杠。
猛不防,出事了——朝粪堆越旋越低的老鹰,突然扇来一股风,像电影里的飞机俯冲,在粪堆上蜻蜓点水似那么一点,扬翅飞去了。
干粪堆被鸡刨了个窝,刚下的白白的蛋,没有了。那时的天空,逢晴日无不瓦蓝,云朵像放大的棉花撕扯洁白,衬着那只黑老鹰。爪间抓的,是我家的那颗鸡蛋。狗日的老鹰很得意,往高里飞了,并不远去,悠闲地在天上盘旋。分明冷笑着在嘲弄人。
我和仲元顾不上在地上顶杠了,跳起来撵着天上的老鹰顶杠。俩人边撵边抡长点儿的柴棒吓它,大声地吆喝着吓。天上的老鹰没怎么着,把连庆家槐树下下象棋的大人惊动了:
啥事?
一只老鹰,把豪子家母鸡下的蛋抓走了。
嘿嘿,那还能要回来!
那只老鹰竟滑翔似的,一直盘旋着。老实话在嘲弄耍笑人呢。气得仲元涨红了圆脸,从后腰背里抽出甩子——用枣木的叉棒和牛皮条做的,怕失手伤人惹祸,平常不拿出来——把手里捏的棋子夹在皮条里,瞄准老鹰,伸手臂狠劲一甩。石子没击中它。仲元又夹又甩。甩来甩去,石子甩光了,都没击中老鹰。他人却滚子似绊地上,跌了个狗吃屎。我顾不上他,狠不得双肩生翅,扑上天去。我撵着跳着,抡柴棒吆喝,一直撵出了村,撵到了涝池旁。
村外的涝池比篮球场大,是村里男人们饮牛、女人们洗衣、碎娃们耍水的好去处。时值正午,当头的太阳正大,涝池边没人影儿。仲元也没跟来。我独自仰脸瞅着老鹰,一时没了办法。又怕冷不防它杀回马枪突然袭击我,便泄气蔫了下来。
恰巧这当儿,意外出现了。
老鹰慌忙中,爪子一松,鸡蛋掉了下来。刷得坠下一道白线,叭一声掉涝池里了。溅起了一朵水花。
我得意失笑了。浑身来了劲,又蹦又跳地笑。可恶的黑老鹰呀,你也有大意失手(爪)的时候。可惜了我家那颗鸡蛋,我得不到老鹰也得不到。站涝池边一看,别提多高兴了。溅水花那儿,没蛋黄溢出,鸡蛋在水纹里隐现,似乎没摔破。水面平静了,我乐得不得了。那颗鸡蛋竟白花花的,在水底淤泥里坐着呢。
池水不深。我抬头仰脸嘲笑老鹰。它却早没影儿了。我高兴地脱鞋,要下水捞蛋。太阳晒得人生痛,捞了蛋,正好耍水。
这当儿,不知多会冒出一辆架子车,正从池边路上经过。土路不平,车上装的生石灰块子太满,有石灰颠下来。其中一块,有足球那么大。拉车子的戴一顶破草帽,穿洋面口袋改做的无袖汗褟的脊背弯下去,弯下去,红红的显出肩背处淡了的标准粉的标字。搁在以往,我会喊住他,或者抱起石灰块子撵上去,给他搁车上的。但那一会儿,被老鹰抓走的鸡蛋要失而复得,我一时得意忘形,没那样作。我抱起足球大的那块石灰,咕通投进涝池。
万没料到,生石灰遇水,咕嘟冒起了泡儿。咕嘟咕嘟越冒越烈。澎得又炸裂开来。我又捡又投。咕嘟咕嘟澎澎,冒泡儿又炸裂。涝池开了锅似煮起来。呛人的蒸气剌鼻,退着躲着仍扑面而来。
我惊呆了。也乐坏了。又躲又迎着煮沸的气味蹦跳欢笑。可惜仲元没来。也没饮牛的洗衣的耍水的村人看见。唯见那位拉石灰的,不知啥时停了车子,从路另一旁的西红柿地里出来,端着的破草帽里,搁着几个刚摘的西红柿,边吃边抹着嘴上的汁液,朝我凶凶地吼:
碎崽娃子,你咋糟沓我的石灰块子呢!
我没糟沓,我说,见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并不害怕。
水都煮开了,还说没糟沓?
我想垫池边捞鸡蛋,谁知……
鸡蛋?
真的。
他吃完了一颗西红柿,抹把嘴,递给我一颗,又拿一颗吃起来。那时侯,过路人口渴了,是可以随便吃地里的瓜果的,只要不糟沓或带走就没事。三两口吃完,他问:
鸡蛋在哪儿呢?
那不是,来到涝池边,我也抹了把嘴,往水里一指。
咕嘟已止住了,池水白了混了。也不知他看到鸡蛋没有,说了句:
那还不煮熟了。
听到这话,我心里打开小鼓。自家没断过养鸡,可煮鸡蛋的美味,我只在端午节领略过。怕他抢了先,我甩脚脱了鞋,挽起了裤腿,要下水捞蛋。
小心烫着。他站一旁急喊。
唉哟,我伸脚探进水,缩回脚呼喊着。一尻子坐地上,捂着脚唉哟着。
你看你,急啥呢!那人说。
我唉哟不已,抖着那只脚。
生石灰见了水,不但会煮沸,还爆炸呢,他说,你刚才没看见?
我瞠目乍舌,不知说什么好。
他捉住我那只腿脚,卷了半边破草帽,往我脚上扇。脚面和小腿脖儿,被烫红了,灼痛难耐。他去了路边的菜地。不一会儿,手里拿了两根黄瓜回来。几下捏碎黄瓜,给我往烫处搽。又将碎黄瓜交给我,叫我自己搽。我抹着黄瓜,却只管一时时。连一秒钟都不到,仍然灼痛得很。他离开又来了。捏着一种草,搁池边洗衣石上,大手握成拳头,几下捣烂,又伸姆指研。抓土和成绿泥,给我往伤处糊。不咋得,忍着点。对我说了,轻轻撩着水,洗了自己的手,说不太烫了,脱了鞋,小心地蹚水,下池捞出那颗鸡蛋,扬起对我说:
真的煮熟了,递来让我剥了皮吃。
大太阳里来来回回地跑了几趟,他给我搽黄瓜又和草药泥涂抹,灰白的汗褟都溻湿了。从他贪婪的盯鸡蛋的目光里,看出他吃西红柿解了渴,却没解饿。想着他还要冒大太阳,拉那么重的一车石灰赶路呢,不知怎么良心发现了,推去他递来的鸡蛋说:
大哥你吃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他说着,不知是饿坏了馋急了,还是觉得我理应领他的情,几下剥了鸡蛋皮,囫囵往嘴里一填。咀嚼动作传向喉结,迅即咽进了肚里。
见我盯着他,他自觉吃相粗鲁,不好意思吧,想了想,从脖后取下胸膛挂的一枚麻钱,说:
听我婆婆说,是开了光的,镇邪呢。
开了光,镇邪?我听不明白。
给,拿去耍吧。他说。
麻钱是铜的,圆中有方方正正的孔,光光亮亮的,显出四个辩不清的字。我接了想问他:啥叫开了光,怎么就镇邪呢。他却说:
我不能耽搁了,你也快回吧。
转身埋头拉了车子,戴着破草帽走了。
我光着伤脚,捏着那枚麻钱,提着一只鞋,望着他往杨家围墙那边走远了,才回的村。
那枚麻钱,我没往脖项上挂,解去了线绳绳,压在枕头下。觉得不保险,又装进黑漆的小木匣子,搁壁上的窑窝里。却忍不住拿出来看,看了趁兴,装衣兜里,好在伙伴们面前显摆。
仲元看了麻钱,稀罕得很,拿手里啧啧着,不想还我了。我一把夺了过来。他就明打明地缠我,非叫给他不可。我不给他,他就叫我赔他的书。
他曾借给我一本怎样吹笛子的书,定价两毛六,不知咋地让我弄丢了。凭我俩的关系,事情已过去了。可这会儿不给他麻钱,他叫我赔他的书。
我硬是在开学后,从家里给的早点钱里,每天省下一分二分,赔够了他的书钱。就这仲元仍不罢休,又向我扯皮说:书钱是赔够了,可你照着书,学了吹笛子呀。我拗不过他,拿我妈染指甲的指甲花汁液,蘸在麻钱上,寻出糊窗户剩下的粉莲纸,裁下巴掌大的一片,拓麻钱的红印儿。一正一反两个面都拓了,给了仲元,才了结了这事。
时间长了,对麻钱的兴趣淡了,见村里女娃爱踢的毽子里,用麻钱做底儿的最好。就给了我妹子,叫她做了毽子。那是一只活公鸡毛做的毽子,颜色鲜艳,底儿因了裹的麻钱,不轻飘,妹子有了它,宝贝似的,踢得很高兴。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年逾知天命的我,把大半人生经历的许多事都淡忘了。少年的回忆,却像高象素的荧幕,越来越清晰。我曾忙中偷闲长途跋涉,独自去小时客居过的那个村造访。悄悄来到异常熟悉的村子,默默地徜徉、徘徊、留连了半日。在原先的村头,现在挂天下第一碗名牌的馆子里,吃了一碗羊肉泡馍,离开了。
村北那条百米宽的道路还在,两条马路之间宽阔的绿化带,如今已树木葱茏花草茂盛,成了市民休闲的场所。村里早先前后村道的布局,彻底改观了面貌。一排排瓦顶土墙的瓦房,消失净尽了。一座座门楼、类堆,一棵棵槐树、榆树,村外的涝池、菜地,天上飞的鸦雀、老鹰,都没踪影儿了。甚至连村名都改了,成了什么城中村。社区里成片矗立起许多高楼大厦,草坪和花圃,栽修剪整洁的花木,人们在蹓狗或给笼养鸟放风。道路都硬化成水泥的,人行道铺有彩色磁砖。熙熙攘攘的超市、饭馆、干洗店、音像店、健美瑜伽房、足浴洗头房之类,门脸都装修得特别现代。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大都说普通话,少数说土语方言的,咬音却变了调。听说连庆从石油学院毕业后,去玉门和大庆开采过石油,后来患上肝癌,已去世多年了。高中毕业后走南闯北的仲元,回市里在博物馆安宁工作了几年,又辞职下海了,现已不知去向。少年伙伴的现况,踏破铁鞋无觅处。
变化不大的,是我在装修新潮的泡馍馆里,掰碎了两个坨坨馍烩了,吃的那一老碗羊肉泡馍。风味依旧,还算正宗。余香满口站在泡馍馆外,燕群似飞来一群学生,着校服骑自行车从面前闪过。注视中我伫立良久,心中感慨万千。
一天,老伴上街了,我独自在家,正百无聊赖,门铃响了。叮咚声中,我以为女儿带外孙女来了,喜悦地问:
谁呀?
是我。随回答声,从猫眼看到的,是一张夸张变形的陌生胖脸。
你找谁呀?
我是仲元。
以为听错了,我又问:是谁?
是我,仲元。
开了门,要不是他自报家门,我真认不出来了,站在面前的,真是仲元。
哎呀稀客,我油然惊叹,连忙让座、倒茶、递烟。
可找到你了。他一屁股坐沙发上,喝茶抽烟,其惊喜比我胜过十分。
因了重访故地归来不久,我说起日前的造访,欲和他热烈地回味,共享沧桑巨变的感慨。仲元对这些反应淡漠。他从提包取出一个皮夹,又从里面急切地拿出一片纸。
竟是当年的那片粉莲纸。
多亏我当时夹日记本里了,至今没有丢失。仲元扬着那片纸说。
是当年我给你的,拓的麻钱印还显着呢。我看了说,诧异他一来,怎么拿出了这。
仲元说:
你细看拓印儿。
我看不出什么,没作声。
他说:去阳台上,反过来,对着太阳看。
我俩站阳台上,对着太阳,高高地反向展开粉莲纸细看。
内方外圆的拓印间,正面呈现的四个繁体字是,咸丰重宝,一面有咸丰元年铸造的字迹。
看出来么?他问。
我不知回答啥。
要不是你,我才不会说呢,仲元说,这枚古币,价值好几十万,宝贵得很呢。
他的话题再没离开这枚古币,一再神情异常追问:你妹子后来把那个毽子弄哪去了,能不能顺蔓摸瓜,下功夫找到这枚古币?事情过去几十年了,我笑着说,肯定找不到了。又说了已在北京居住多年的妹妹的简况,提起日前造访旧地的感慨。他先还让我给妹妹挂长话,叫她仔细回忆,后来便一声接一声地感叹,充满了惋惜和失望,以及深深的遗憾。
我也很遗憾。这次意外重逢,他的兴趣在那枚古币上,没有重温少年时甜蜜的童贞趣事,更没品味时尚多变的人生体验。他没在我家吃饭,就匆匆告辞了。甚至没留下地址和联系电话,临别时只说,你和你妹妹好好回忆回忆,以后我还会找你的,要是得到确切的线索,大海捞针我也要找到它。
老伴回来,我向她细述了仲元来家的情景,道出了心中的厌倦。老伴惊讶仲元是如何费尽周折找到这的,轻轻地叹了声:世道么!其话语简练模糊,浓缩了深沉的况味。
打那以后,我和仲元再没见过面。恍惚中听谁说,他出国了,到澳大利亚定居了。
后来,退休在家的我和老伴,常常谈起彼此婚前的往事。我不免一遍又一遍重述关于古币的趣事。老伴重复地听我讲顶杠,老鹰抓鸡蛋,生石灰煮沸涝池,以及得到麻钱的细节。竟然百听不厌。她的那句:世道么,慢慢淡化了我骤涌的遗憾。
要说遗憾,至今仍有一点,是关于那位拉石灰的大哥。他帮我应急疗治脚上烫伤的情景历历在目,当时怎么没问他的住址和姓名呢?不然的话,我要用仲元大海捞针寻找古币的精神找他,和他交友,与他长谈。遗憾之余,我心里常常于无声处发出旷世般地呼唤:
拉石灰的大哥,你在哪里呀?
欢迎转载趣闻堂的文章,请注明出处:趣闻堂 (quwentang.com)
相关推荐

探秘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诡异的相遇,
阅读(10)

失踪的李大山
阅读(8)

失踪的丽妇
阅读(6)

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怪事:村里的那口老井!
阅读(8)

迟解的诅咒
阅读(6)

求婚的手段
阅读(4)

神秘的青蛇寨
阅读(4)

蛇腹脱险的士兵
阅读(4)
趣闻随便看

全球奇葩Top5:让鳄鱼咬一
阅读(4)

生活中的7件小事让你错失
阅读(7)

神奇!盘点地球上五种没
阅读(8)

摄影师和座头鲸趣味同游
阅读(10)

还没适应手机砍掉3.5mm耳机
阅读(11)

人类换头术能否成功?这
阅读(9)

虐死单身汉“春天到了,
阅读(7)

中国夫妻最缺什么?说得
阅读(9)

洗手很费水,换用空气洗
阅读(1)

想生双胞胎也有技巧的?
阅读(10)
7天热门

童话变真实?沉睡500年的
阅读(178)

四大超时空悬案
阅读(155)

不可思议的“神秘地带”
阅读(78)
特别推荐

UFO再次靠近国际空间站,
阅读(8)

震惊科学界!阿根廷惊现
阅读(4)

15个让你大开眼界的水果切
阅读(6)

惊讶!17岁少年心跳停了
阅读(10)

万圣节装扮最大赢家是孕
阅读(1)

比百慕大更真实的存在!
阅读(4)

牙医帮你纠正7个错误刷牙
阅读(4)

当科技和舞蹈结合在一起
阅读(2)

9个改变自己的细节
阅读(7)

脱口秀主持人台上被殴打
阅读(6)

他醉酒照被传到网上后,
阅读(15)

这女子每年花费1.15万英镑
阅读(10)
 趣闻堂
趣闻堂